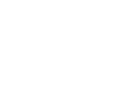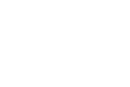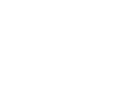1981 年,粟裕将军因病住进了北京 301 医院。岁月不饶人,这位从前在战场上纵横驰骋、让敌人丧魂落魄的名将,此时已被病痛折磨得身形瘦弱。
一天,堂弟粟多瑛特别前来看望。粟裕躺在病床上,见到亲人,暗淡的目光里瞬间有了光,他伸出弱不禁风的手,紧紧拉住粟多瑛,嘴唇轻轻哆嗦,用略带沙哑却满含厚意的声响问道:“多瑛啊,后山那片枫树还在吗?”
粟多瑛心头一酸,眼眶瞬间湿润了。他怎样也没想到,堂兄在病重之际,心心念念的竟是家园的那片枫树林。他用力抓住粟裕的手,连连允许说:“在呢,哥,枫树都长得好好的,一到秋天,仍是满山红叶,美丽得很。” 粟裕听了,嘴角轻轻上扬,似乎陷入了长远的回想,目光中透着无尽的留恋。
粟裕生于湖南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,家里是地主,尽管后来家境逐步不如往昔,但在当地还算富裕。他的父亲是个落第秀才,满脑子封建思想,一心想让粟裕管家记账,承继家业。可粟裕打小就对那些绿林好汉、行侠仗义的事儿感兴趣,底子不肯被家里的账本捆绑。
家里有个长工叫阿陀,比粟裕大十多岁,会功夫,还知晓各种江湖传奇。粟裕成天缠着阿陀,让他讲侠客故事,像 “草上飞”“一枝梅”,听得如痴如醉,满脑子都是闯荡江湖、除暴安良的想法。在阿陀影响下,粟裕练起了 “飞毛腿” 功夫,还学骑马、做火枪,就盼着有朝一日能像侠客相同,惩治人间不平。
那时候,社会动荡不安,军阀胡作非为。粟裕上学时,会同县城驻着军阀的一个连,连长和手下整日在城里横行霸道,大众苦不堪言。粟裕和同学们气不过,常常跟军阀的兵 “斗智斗勇”。有一回城隍庙唱戏,军阀的兵成心挡在学生前面,两边起了抵触,学生们抄起家伙抵挡,尽管吃了亏,可也让粟裕更坚决了要拉起一支部队,把这些坏蛋赶跑的决计。
父亲给他组织了一门婚事,女方家境不错,年岁还比他大几岁,粟裕心里一万个不乐意。1924 年,县里选拔学生去常德省立第二师范考试,粟裕考上了,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去。粟裕骨子里有股顽强劲儿,悄悄离家就往常德走。走到半路,发现旅费不行,他一咬牙,给家里写信,信里就一句话:“讨米也要走!” 父亲见他决计这么大,毕竟仍是心软了,凑了路费,让哥哥送他起程。这一年,粟裕才 16 岁,就这么当机立断地脱离了家园,奔赴不知道的出息,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新浪潮之中。
自 1927 年参与南昌起义起,粟裕就踏上了这条充溢艰苦与荣耀的革新之路。起义失利后,他跟着朱德、陈毅上了井冈山,在那片赤色的土地上,阅历了很多次严酷战争,也逐步生长为一名坚毅勇敢的兵士。
长征期间,他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,带着部队在刀光剑影中络绎,为赤军主力控制敌军,哪怕屡次深陷绝地,也从未不坚定过心中的信仰。在一次激战中,他头部中弹,几乎丢了性命,可刚养好伤,就又奔赴战场。
抗日战争时期,他带领新四军健儿活泼在江南敌后,黄桥战争、车桥战争,一场场成功让日军丧魂落魄。他的战术灵敏多变,常常出乎意料,打得敌人晕头转向,为捍卫疆土、抗击外敌立下赫赫战功。
解放战争中,他更是大放异彩,苏中战争七战七捷,莱芜战争、孟良崮战争、淮海战争…… 一个个经典战例,都是他军事才干的绝佳展示。面临数倍于己的强敌,他运筹帷幄,指挥若定,以少胜多,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多年征战,他身上留下了很多伤痛,可他从未有过一丝畏缩,一直据守在战争一线。
其实,这现已不是粟裕第一次巴望回乡了。自从 1924 年脱离家园,投身革新,战火纷飞中,回乡之路变得无比绵长。
1949 年,渡江战争前夕,陈毅关心地问他:“老伙计,离家二十多年了,想不想家?” 粟裕眼中闪过一丝迷惘,随即坚决地说:“家中老母、兄弟姐妹,我怎能不想?可现在战事正紧,唯有成功,才干给家人最好的告知,等全国解放,我定要回家看看。” 后来家园解放,陈毅提议派兵护卫他回去,粟裕却因战事繁忙、不肯劳师动众,婉拒了这番善意,再次与家园擦肩而过。
1958 年,粟裕到长沙作业,恰逢家园县长也在。问询家园状况后,他流露出想顺路回乡之意,可传闻家园正全力投入 “”,他忧虑影响出产,又把这份怀念深埋心底。
多年来,粟裕只能凭借着家园亲人寄来的相片,安慰心中的怀念。相片里的老屋、山水,重复看了很多遍,那些了解又生疏的画面,成了他在异乡据守的精力寄予。现在躺在病床上,身体的衰弱与心灵的巴望交错,让他对家园的怀念益发浓郁,那片承载着儿时欢喜的枫树林,成了他心心念念的挂念。
终究,粟裕仍是没能再踏上故乡的土地。1984 年 2 月 5 日,这位为新中国立下永存勋绩的名将,带着对家园的无尽留恋,永久地脱离了人世。遵循他的遗愿,骨灰撒在了他从前战争过的当地,其中就包含家园的那片热土。
粟裕尽管没能重回故乡,但他的精力却永久鼓励着家园的人们。在会同县,他的故事代代相传,那片枫树林也成了人们思念他的标志。他用终身诠释了为国家、为公民舍小家、为我们的崇高情怀,这份情怀好像一座永存的丰碑,矗立在人们心间,让后人永久铭记他的功劳与对家园深重的爱。
![{_CFG[site_title]}](/ms/static/picture/20200317021300859.png)
![{_CFG[site_title]}](/ms/static/picture/20200317020349995.png)